

北京时间10月4日下午,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被授予科学家阿兰·阿斯佩(Alain Aspect),约翰·弗朗西斯·克劳泽(John F.Clauser)和安东·塞林格(Anton Zeilinger),以表彰他们“用纠缠光子进行的实验,建立了贝尔不等式的违反,并开创了量子信息科学”。
在哪里改一改
1975 年至 1982 年

阿兰 ·爱斯派克特( 1947— )
欧洲核子研究中心,贝尔办公室大门附近悬挂着一张莫迪利亚尼作品的画报,上面是一位戴着帽子、脖颈修长的女子,她的目光和贝尔的目光都注视着 27 岁的阿兰·爱斯派克特——一个长着大胡子的和善的研究生,他正在热切地谈论着水箱。
那是 1975 年初,爱斯派克特刚刚结束在法国的三年短期“兵役”,期间他一直在喀麦隆教书,然后回到了欧洲。他刚一回来,就经历了他所谓的“一见钟情”。
他回忆说:“1974 年 10 月,我读了贝尔那篇的著名论文《论爱因斯坦 – 波多尔斯基 – 罗森佯谬》,我对它一见钟情。

这是我做梦才能想到的最令人激动的课题。”他马上决定在母校——位于奥赛的巴黎南大学,把贝尔定理作为自己的博士研究课题。
此时,克劳泽正在努力找工作。“我至少已经向十几个地方提出了申请,结果一概被拒绝了。”高校不愿意聘请一名鼓励下一代人质疑量子理论基础的教授。
最终,在位于美国奥克兰东部群山中的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,克劳泽找到一个空缺,研究等离子体——这是戴维 ·玻姆的首要爱好。
在面试的时候,克劳泽声称:“我根本不懂等离子体物理,但对于做物理实验,我懂得很多,我是个很有才能的实验物理学者。”
他得到的答复是:“你可以学习等离子物理。”他于 1976 年被聘用,并在那里待了 10 年。在利弗莫尔,作为实验学家,他自命不凡的技能得到了很好的应用,但也几乎荒废了一项同样优秀却没声明过的技能。

克劳泽有种天赋,即使在教师行业中也很少见:他能向学生清晰、生动、耐心地解释复杂难解的知识。自从业以来,在 30 年时间里,克劳泽从来没有找到过一所大学,能发挥他所有的才能。
弗莱在 2000 年解释说:“回顾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,著名的物理学家们不喜欢提出有关量子力学的问题。我觉得,克劳泽多少受到了这种思潮的冲击——我认为,这是由于他实实在在地在做实验,而不是只讨论理论问题。”
弗莱自己在学术上运气很好,在他做实验做到一半的时候,就获得了终身职位。30 年后,弗莱已是得克萨斯 A&M 大学的物理系主任。
他得知,学校做出这个明智的决定,还多亏了霍尔特在哈佛的导师弗兰克 ·皮普金的介入。弗莱的一个朋友得知,大学任期委员会本打算否决这名贝尔实验者,于是请来了皮普金教授。
皮普金对委员会说:“如果你只拿埃德的档案给我看看的话,我会很快否决他;但是如果用一天时间看他做实验,我会告诉你,这家伙很优秀。而且,我敢断定,他会成功的。”皮普金在原子物理上的声望战胜了委员会的质疑。
与贝尔定理相关的实验已经背负了恶名,贝尔自己也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 点,但爱斯派克特却一直没意识到。
1972 年前往西非之前,爱斯派克特回忆说:“在经典物理学方面,我受到了相当好的教育,但我知道,自己在量子物理方面受到的教育是很差的。”他在这方面上过的课中,解方程时几乎不讨论物理意义,更别说任何有理论缺陷方面的教导了。
在靠近赤道的喀麦隆的三年时间里,爱斯派克特自学了量子力学。他用的是伟大的法国物理学家克劳德 ·科恩 – 塔诺季奇新写的一部教材。

爱斯派克特认为,这本书有两大优点,“第一,它是真正的物理学;第二,关于基础理论,它是中立的,没有给人洗脑的意味,没有说‘玻尔解决了一切问题’。”最后,他说:“我能解这些方程了,而且没被洗脑。”
爱斯派克特说:“我完全信服爱因斯坦和贝尔。”但是该做什么实验呢?在重读贝尔 1964 年发表的论文时,爱斯派克特发现文章的最后几行告诉他“仍然有一个重要的测试需要做”。
爱斯派克特飞快地跑到日内瓦,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贝尔。
贝尔在文章的结尾处用了一条警示性的注释。如果一个光信号有足够的时间来联系粒子,那么,纠缠将失去大部分神秘性。
贝尔写道,以光的速度交换信号才能 “对仪器进行充分设置,让它们达到某种相互协调”后,量子力学才可能令人信服地起作用。“
在这种关联中,波姆和阿哈朗诺夫(在 1957 年)提议的那种实验至关紧要。在实验中,实验设置在微粒飞行期间做了改变。”
这个实验的实际难题是:每个弗里德曼 – 克劳泽装置末端庞大、易碎的玻璃起偏堆无法迅速移动到设定位置。对此,爱斯派克特提出了一个漂亮的(也是重要且廉价的)替代方案,设置的主要成分是水。

爱斯派克特向贝尔解释说:“每个偏振器由一套包含一个转换开关装置,及其后面位于两个不同方向的偏振器代替。”
在任意给定时刻,开关只打开通向其中一个偏振器的通道。“该转换开关将迅速使入射光从一个偏振器转向另一个偏振器”,不给光速信号留有导致仪器两端进行任何“协调”的时间。他转身朝向黑板,在上面写下了“如果两个开关毫无关联地随机运转”这种情况下适用的不等式。
爱斯派克特的“转换开关”是两个装满水的玻璃箱,两者之间的距离在 42 英尺以上,分别位于产生光子的级联钙原子束的两侧,每个水箱都载有一种远高于人类耳朵听觉能力的声波(位于水箱两端的变频器将电信号转变成这种超声波)。
声波与光波不同,它需要一种介质,因此仪器外部空间很安静。在所处的介质中,它们通过反复压缩舒张来运动。爱斯派克特的超声波在快速震荡的加强点和平坦的减弱点之间轮转,加强点使水出现疏密相间的条纹斑图,减弱点不对水产生影响。
条纹斑图就像衍射光栅一样能使光产生偏折,从而射到旁边的偏振器上;不存在条纹斑图的时候,光就直接穿过去,射到主线的偏振器上。水波在条纹与均一态之间迅速变换,爱斯派克特解释道:“两个通道之间的转换大约每 10 纳秒就出现一次”,这比光子在加热炉与水之间 21 英尺的距离上传播要快 4 倍。
他承认,这不是一个完美的计划,“因为它的变换不是真正随机的,更像是类周期的。不过,在两边的两个转换开关将被不同频率的发生器控制”。这意味着,两个水箱将以不同的速率振荡,而且在实际过程中频率会产生漂移。
爱斯派克特说:“那么,自然可以假设它们在以一种毫不关联的方式运行。”爱斯派克特热切地完成他的描述后,他静静地站着,等着贝尔回答。贝尔略带讽刺地问了他第一个问题:“你有终身教职吗?”
爱斯派克特只是一名研究生,但由于法国体制的独特性,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职位实际上就是永久性的,这让他与美国同行形成了强烈对比。但即使有这个有利条件,他要做的事也是不容易的。
贝尔警告他:“你会经历严酷的斗争。”但是,恶名不是他担心的唯一问题:“一个人不应该把所有时间都花在研究概念上。你是一个实验者,这会让你脚踏实地,所以你不会处于危机境地;而我,我是一个理论家,我必须把个人爱好留给这个课题。
“如果你终日思考这个问题,你就有发疯的危险。”
弗里德曼逐渐淡出了贝尔物理学,但他发现,即使在 30 年以后,这一实验课题仍然萦绕在他心头。“贝尔实验是个毫无价值的实验(这是个测量结果与预期 没有偏差的实验)。
在我参与其中的那段时间里,我已经做了 24 次没价值的实验,结果发现,你不希望出现的那些事情事实上也确实没有出现。这就是我开启事业的方式。”
正如弗里德曼在 2000 年所说的,他在事业上“不变的主题”是“假如你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,那确实帮助很大:如果你没得到正确结果,你可以猜测是不是实验仪器出了什么问题——那或许就是问题的所在”。
弗里德曼笑了笑,说:“由于迈入了一个正在发生着激动人心事情的领域,我获得了很大的声誉。然后,没发生任何有意义的事,我就离开了。”然而,最后一句话是不可言传的。
霍尔特也把贝尔和 EPR 理论抛在了身后,而转投“面包加黄油”物理学,他的仪器原本就是为此而设计的。他开始了一个新事业,通过级联光子测量原子寿命,利用激光测量光谱,以及测量对于量子力学来说很难解决的原子能级(实际 是除氢原子之外的任何原子)。
回顾以往,霍尔特说:“可以说,我在 CHSH (克劳泽 – 霍纳 – 奚模尼 – 霍尔特)中只是一个小角色。”然后,他笑了笑,“但我的错 误结果却轰动一时。”

随着弗里德曼的淡出,这段经历让霍尔特开始思考科学如何前进。“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科学法则:一个错误的答案较之于刚好在课本中找到的答案,总能使相关领域变得更刺激——一个错误的结果令人们兴奋。真头疼。
“显然,你并不希望发生那样的事——一个理论学家提出一个猜测性的新理论,再被推翻也不错。但一个实验学家应该非常谨慎,其误差限度应该是合理的。
不幸的是,在这个实验中,无论你在何时寻找强相关性,任何一种你能想象到的系统误差都会将之削弱,并使之指向隐藏变量的范畴。这是个艰苦的实验。
在那些日子里,我已经用这类设备试过各种速率……我能说什么呢?”他耸了耸肩,笑着说, “我把事情搞砸了。”
然而,到底哪个实验是对的,并不像这些实验要阐明的量子力学那样清晰。霍尔特说:“问题是,我是名科学家,我倾向于相信答案就是大自然的话,而不是只要想一想,就能提前知道的那些东西。并且,我一直认为量子力学是美妙的,因为它是一个奇迹——”他笑着说,“它是一种我们这些‘科学祭司’能发现的秘密知识……”
他解释说:“这并不是说我要保守秘密,但如果一切都那么显而易见,如果你仅 仅四处扫一眼就能看懂整个宇宙,那就没什么意思了。量子力学很微妙——这就是 它的魅力。
“对我来说嘛,我在物理学上的所有兴趣,都是因为自己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……并且,”他简单而略带希望地说,“我现在还不知道答案……这是件令人沮丧的事……我认为还要用很长时间,人们才会明白量子力学的内涵。
现在所有这些实验清楚地表明:你至少必须暂时接受,要用量子力学的方式去思考观察不到的事物的状态。而且,至今这还是一件不令人满意的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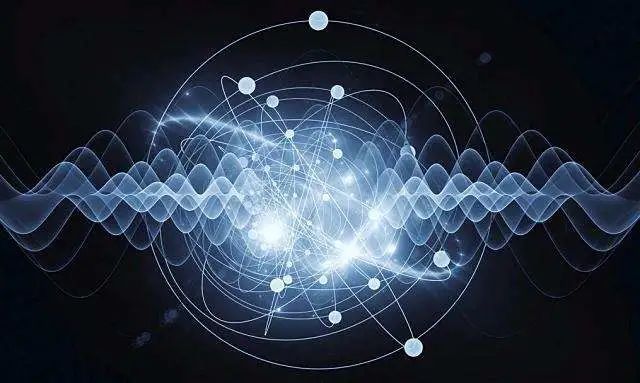
“量子力学仍然是——无论怎么说,它都是一个未竟的事业。但我相信,事情会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上取得突破……我们可能根本不必去解决那些原先出现的问题。这些问题会在某一天消失,因为我们会发现,也许是我们问错了问题。”
1975 年,迈克 ·霍纳也认为自己正在离开贝尔物理学。他和奚模尼迷恋上了 一套漂亮的新实验仪器——赫尔穆特 · 劳赫刚刚在维也纳发明的中子干涉仪。与克劳泽实验展示了光的粒子性形成鲜明对比,劳赫的仪器戏剧般地展示了物质的波动性。
就如霍纳生动地描绘的那样,在 19 世纪的最初几年,伟大的物理学家托马斯 ·杨“用实验显示,两束相同亮度的光的叠加(或重合)能够产生黑暗。而且,在稍微不同的条件下,还能使它达到任意一束光亮度的四倍”。
霍纳笑着说:“这就是说,1 加 1 等于 0,但是在其他条件下,它等于4。”这被称为干涉,它意味着波的存在。
但是,劳赫正在用实物粒子展示这些波动现象的特性。产生于核反应堆中沸腾热核的大量粒子、中子束,像波一样互相干涉着。
中子干涉仪为中子提供了两条可供选择的 V 形路径,这就像一个孩子选择通过地面或天花板,将球反弹给他的朋友。不管怎样,中子进入干涉仪后,撞击到 “地面”或“天花板”,它最后的终点是一样的。
因此,起点相同但路径不同的两个中子,后来将再次相遇。两条路径一起来看,就勾勒出一个菱形。当中子相遇时,它们就会相互干涉。
令人关注的是,即使是单个中子进入干涉仪,它也会与自己发生干涉。这和许多量子力学难题一样,是难以描绘的,它就好像是一个中子同时在两条路径上传播一样。
霍纳和奚模尼沉浸在两个粒子的神秘纠缠中已经有 10 年了。现在,他们被这个不可思议的单粒子效应搞得心烦意乱。霍纳回忆说:“阿伯纳和我都认为,这将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装置,人们将会对它玩味研究多年。”
刚一开始,霍纳和奚模尼就意识到,它能够用来演示自旋为 1/2 的粒子,比如中子,只有当它在某个位置旋转两周后,才会回到初始位置。这种令人兴奋的可能性也引起了其他关注量子力学 基础的人的兴趣。
在奚模尼与霍纳发表论文之前,从他们那里沿马萨诸塞州收费公路向南,在阿默斯特校区的赫伯 ·伯恩斯坦也提出了这个实验建议。劳赫立即与一位与霍纳年龄相仿的年轻奥地利物理学家安东 ·泽林格在维也纳进行了这个实验。
不久后,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埃里塞举行的贝尔物理学研讨会上,泽林格再次露面。霍纳记得,包括贝尔与奚模尼在内的 15 个或 20 个与会人员中,“只有一个人没有谈论两个粒子(他谈论的是单个粒子),他就是安东”。
如今,霍纳也对单个粒子感兴趣,他回忆说:“我们立刻就很投缘了。”一个说话柔和的美国南方人和一个魅力超凡的奥地利人,两个大高个子的长着胡须的男人惺惺相惜,进行了深入交谈。

霍纳回忆说:“我们一起讨论了很多天,他开始向我介绍中子干涉测量的细节,我告诉了他很多那时候他显然没有参与的事情……”
泽林格回忆说:“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国际性科学组织。在那里,我第一次听说贝尔定理、EPR 佯谬、纠缠等诸如此类的概念。不用说,我不能真正理解这些概念都是什么,但是我有预感,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。”他已经着迷了,努力从霍纳那里学习关于纠缠的所有知识。
当霍纳回到家,他径直来到克里夫 ·沙尔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——他听说过那里关于中子干涉测量的传闻。著名的沙尔,身高比霍纳的一半高一点,他受人爱戴,开创了中子衍射的研究领域——对明显是粒子的中子的波动特性加以利用。
沙尔在 1975 年完成的这项工作于 20 年后为他赢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。当奖项颁发下来的时候,他的合作者厄尼 ·沃伦已经去世了。
霍纳对沙尔说:“我听说,你正在建一个叫中子干涉仪的小型基础量子仪器,我想用用!可以吗?”
沙尔回答:“当然可以。把那张桌子搬到那边去。”
霍纳回忆说:“这样,我刚好能坐下来。从那之后,每个星期二我都去那儿 (我星期二在石山学院没有课),而且在接下来的 12 年里,在周末、每个节假日、 圣诞节假期和暑假,我经常去那儿。”
对于一个既不是理论家也不是实验家的人来 说,“我恰恰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那种人,或者说,两者兼具。”那真是“有趣的 12 年。当他们想去搬铅块,我就和他们一起去搬铅块”。而当他们需要深刻的洞察力来计划实验的细节时,随和的霍纳也擅长于此。

霍纳在沙尔的实验室里开工后不久,泽林格也露面了。他和家人一起来了美国。泽林格一心要做中子干涉测量实验,而且就像霍纳笑着回忆的那样,一心要买 “他能得到的美国最大的汽车——奥兹莫比出产的‘陆地巡洋舰’,真的像游艇一样 大的货车”。
接下来出场的人是丹尼 ·格林伯格(实际上,他是回到了母校),一名来自布朗克斯的诙谐、矮胖的纽约人。自从几年前中子干涉仪被发明后,他就开始追踪。他曾想去研究引力对一个中子干涉的影响——几乎在中子干涉仪刚刚投入使用后,这个实验便开始在密苏里州起步了。
在最初的一次中子干涉测量讨论会上,格林伯格见到了霍纳和泽林格,他记得:“我们出奇地投缘,所以我开始定期去麻省理工学院。并且,克里夫非常支持我们三人。”沙尔是“一个可爱的人”。
格林伯格把出访实验室的那 10 年称为他 “职业生涯中的巅峰,可以说,和很棒的同事做趣味十足的事,很有意思”。这场历经 10 年的探索,将发现比以往更加奇异的三个粒子的纠缠。
0 条评论